自紫杉醇發(fā)現(xiàn)以來的半個世紀里,絕大多數(shù)紫杉醇合成相關基因均由歐美研究團隊主導完成。今天,這一情況得到改變。
北京時間1月26日凌晨3時,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科學》在線發(fā)表了中國農業(yè)科學院深圳農業(yè)基因組研究所研究員閆建斌領銜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巴卡亭III生物合成酶的鑒定與異源重構”。研究發(fā)現(xiàn)了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徑中的兩個缺失的關鍵酶“T9αH1”“TOT1”,闡明了關鍵結構分子——紫杉烷氧雜環(huán)丁烷的形成機制,打通了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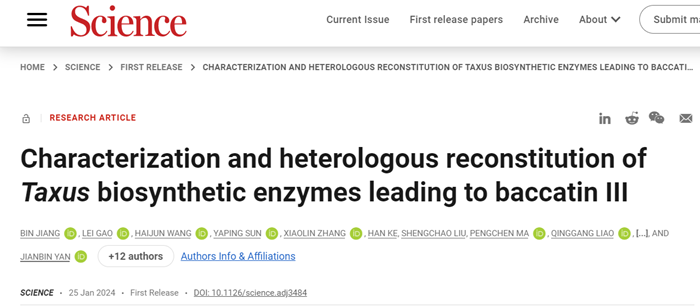
“紫杉醇異常復雜的化學結構決定了生物合成途徑解析的空前難度。”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國屏表示,這一研究成果標志著我國在天然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徑解析以及人工底盤通路重構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中國科學院院士鄧子新認為,該研究實現(xiàn)了紫杉醇合成生物學領域的引領性原創(chuàng)成果重大突破。
紫杉醇的生物全合成研究尚未實現(xiàn)
紫杉醇是著名的植物抗癌天然產物藥物,廣泛應用于乳腺癌、卵巢癌等多種癌癥的臨床治療。
然而,天然紫杉醇來源稀缺且單一,僅能從珍稀瀕危裸子植物紅豆杉中提取。如何不依賴紅豆杉實現(xiàn)紫杉醇的生物合成?
自上世紀80年代起,科學家便開始尋找一種可以替代天然提取紫杉醇的合成方法。1990年,美國率先研發(fā)出一條紫杉醇半合成路線,并迅速投入商業(yè)化生產。在此后的30余年里,全球上百個科研團隊相繼投入到紫杉醇的生物全合成研究中,但均未能實現(xiàn)突破。
找到兩個關鍵的酶
經過多年的潛心鉆研,中國農業(yè)科學院深圳農業(yè)基因組研究所的研究團隊終于攻克了這個科學難題。他們開創(chuàng)了一種既不需要消耗天然紅豆杉資源,也不需要依賴土壤種植的環(huán)保且可持續(xù)的生產方法。
2021年,閆建斌團隊領銜繪制出了國際首張染色體級別的南方紅豆杉高質量參考基因組圖譜。這張圖譜就像一張“藏寶圖”,揭開了紅豆杉合成紫杉醇的遺傳密碼,為解析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徑提供了寶貴的基因組學指南和關鍵線索。這項研究成果作為封面文章刊登于國際期刊《自然-植物》。
閆建斌介紹道,在這張圖譜的指引下,研究團隊進一步篩選了58個紫杉醇生物合成的關鍵候選基因。最終他們成功發(fā)現(xiàn)了能夠催化氧雜環(huán)丁烷環(huán)合成的細胞色素P450酶,并給它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TOT1。
然而,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科學家們一直未能鑒定出催化紫杉烷C9位氧化的酶,原因就在于難以分離出C9位未被氧化的中間體。
面對這個難題,研究團隊并沒有放棄,而是另辟蹊徑。他們創(chuàng)造性地構建了一個紫杉素的生物合成植物底盤,并利用這個底盤和生物信息學分析,從17個候選基因中成功篩選出了負責紫杉烷C9位氧化的酶T9αH1。這個基因就像是一個隱藏在紅豆杉9號染色體上的寶藏,被兩個已知的紫杉醇合成基因T2αH和T7βH守護著。
酶T9αH1的發(fā)現(xiàn)不僅解開了科學家們心中的謎團,更為紫杉醇的生物合成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
“在閆建斌教授領銜的這項研究中,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一種參與重要抗癌藥物巴卡亭生物合成的重要酶。這一發(fā)現(xiàn)是我們對復雜天然產物生物合成理解的重大突破,它將使我們有能力大規(guī)模生產其他有價值的天然產物,從而開發(fā)出有價值的新藥。”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終身教授,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院院士延斯·尼爾森表示。
巴卡亭III的生物合成之旅
在克服了關鍵酶缺失的難題后,研究人員巧妙地運用了人工異源合成途徑的策略,將新發(fā)現(xiàn)的酶與已知的合成酶巧妙地組合在一起。經過無數(shù)次的嘗試,終于在植物底盤中成功生成了巴卡亭III,這是紫杉醇生物合成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中間體。
閆建斌介紹,結合亞細胞定位分析等實驗結果,研究人員繪制出了巴卡亭III的完整生物合成路線圖。這個過程就像是一場精心編排的舞蹈,起始底物在葉綠體這個舞臺上被酶催化成紫杉二烯。隨后,紫杉二烯通過質體與內質網的接觸點優(yōu)雅地轉移到細胞質中。在這里,它受到了內質網錨定的六個氧化酶和兩個細胞質定位的酰基轉移酶的協(xié)同催化,最終變身為巴卡亭III。
“自1971年紫杉醇結構鑒定以來,其生物合成途徑一直沒有打通。”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曉亞認為,該研究是植物代謝生物學與合成生物學領域的重大突破,為利用合成生物學技術實現(xiàn)紫杉醇的綠色可持續(xù)生產鋪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