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jì)五十年代,郭予元院士從北京遠(yuǎn)赴西北,扎根于祖國(guó)最需要的地方,他一生治學(xué),立足實(shí)踐,攻克一道又一道科技難題,為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科技走向自立自強(qiáng)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3月29日,在我國(guó)已故農(nóng)業(yè)科學(xué)家、中國(guó)工程院院士郭予元誕辰九十周年紀(jì)念活動(dòng)上,中國(guó)工程院院士、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黨組成員、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吳孔明說。
郭予元是我國(guó)植保科學(xué)的領(lǐng)路人之一,1933年生于上海,2001年當(dāng)選中國(guó)工程院院士,2017年在北京去世。此次紀(jì)念活動(dòng)包括郭予元院士銅像揭幕儀式、郭予元院士學(xué)術(shù)思想研討會(huì)等。郭予元院士的銅像將安放于他生前工作的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植物保護(hù)研究所內(nèi),以彰顯老一輩科學(xué)家的精神,激勵(lì)后學(xué)。

郭予元院士銅像揭幕儀式。中國(guó)農(nóng)科院植保所供圖
出身大家庭,童年卻備受磨煉
1933年,郭予元出生在上海一個(gè)大家庭。他在自述中記錄,父親曾是屈臣氏汽水公司的總經(jīng)理,因經(jīng)營(yíng)不善和擅自捐助上萬銀元給精武體育會(huì)等原因,賠光了股份,家道中落,于郭予元三歲時(shí)破產(chǎn)。幼年的郭予元備經(jīng)磨難,父親破產(chǎn),又遭上海淪陷,日寇鐵蹄踐踏黃浦江兩岸,家里的生活每況愈下,只能靠變賣東西維持。內(nèi)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使得他從小就懂得了人生的艱難,知道了國(guó)家貧窮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上海讀高中時(shí),連續(xù)三年六個(gè)學(xué)期他都是年級(jí)第一名,對(duì)此學(xué)校免收了學(xué)費(fèi)。1949年,上海解放,郭予元迎來了自己一生中難忘的秋天——他同時(shí)報(bào)考了5個(gè)名牌大學(xué)并被全部錄取。他選擇了清華大學(xué)昆蟲系,后因院系調(diào)整,清華大學(xué)昆蟲系和其他一些院系合并至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他成為一名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的學(xué)生。
從清華到農(nóng)大,郭予元不大情愿,但又無可奈何。然而,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尤其是下鄉(xiāng)實(shí)習(xí),看到漫天的蝗蟲瘋狂地吞食著莊稼,看到農(nóng)民在因蟲害絕產(chǎn)的田頭落淚,在農(nóng)民的土炕上聽他們講對(duì)擺脫貧窮能吃上飽飯的渴望之時(shí);坐在寬敞明亮的農(nóng)大教室里聽國(guó)內(nèi)一流的農(nóng)業(yè)學(xué)者劉崇樂、陸近仁、胡秉芳等先生授課之時(shí),他的思想發(fā)生了變化。“我們這一代人,能在工作中注重理論與實(shí)踐相結(jié)合,不怕苦,不怕累,能和農(nóng)民打成一片,深入田間調(diào)查研究的學(xué)術(shù)作風(fēng),和我們?cè)谛F陂g受到的教育有密切關(guān)系。”郭予元在自述中說。

2005年在中國(guó)農(nóng)科院植保所溫室,郭予元院士觀察棉花上的害蟲。中國(guó)農(nóng)科院植保所供圖
駐扎大西北,常年駐村治理病蟲害
1953年,郭予元大學(xué)畢業(yè),當(dāng)時(shí)抗美援朝尚未結(jié)束,“既然不能去抗美援朝流血保衛(wèi)祖國(guó),就應(yīng)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建設(shè)祖國(guó)”。在畢業(yè)志愿表上,一直為沒能夠參軍到朝鮮前線而遺憾的郭予元寫下“到祖國(guó)最需要的地方去”。就這樣,他被分配到了位于大西北的寧夏銀川。
1953年的寧夏銀川,沒有一條柏油路,沒有一座樓房,吃水靠牛車送。郭予元被分到了省農(nóng)技推廣站,后被派下鄉(xiāng)蹲點(diǎn),當(dāng)時(shí)沒有公交車,近靠步行遠(yuǎn)騎單車,帶上行李用具在土路上一騎就是一百多公里。他吃住在農(nóng)民家里,白天下地了解病蟲害的情況,向農(nóng)民學(xué)習(xí),也向他們推廣防治技術(shù)。
寧夏作為引黃灌區(qū),水稻是主要農(nóng)作物之一,郭予元在銀川時(shí),稻瘟病連年大發(fā)生。為了研究這種病的防治方法,1955年組織調(diào)他到農(nóng)業(yè)試驗(yàn)場(chǎng),負(fù)責(zé)解決稻瘟病問題。他常常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四五個(gè)小時(shí),稻田里施的羊糞在烈日下發(fā)酵,使他的腿上長(zhǎng)滿了膿包,當(dāng)?shù)厝私醒蚣S疙瘩,遠(yuǎn)看像是穿了一雙黃靴子,刺癢難熬。
郭予元“穿著一雙黃靴子”,每天走十多個(gè)田塊觀察病情、搞盆栽、查文獻(xiàn),到氣象站查資料分析天氣與病情變化的關(guān)系,自學(xué)統(tǒng)計(jì)分析,最終提出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藥劑防治技術(shù)規(guī)范。
引領(lǐng)植保學(xué)科發(fā)展,用科技改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在寧夏,郭予元還領(lǐng)銜攻關(guān)麥種蠅及其他小麥病蟲害的防治技術(shù)。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植物保護(hù)研究所所長(zhǎng)陸宴輝介紹,郭予元在六十五年的職業(yè)生涯中,為我國(guó)植保學(xué)科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他引領(lǐng)性地創(chuàng)建了適用于植保科學(xué)試驗(yàn)的一套統(tǒng)計(jì)分析方法,對(duì)植保試驗(yàn)的科學(xué)設(shè)計(jì)和統(tǒng)計(jì)分析、病蟲害的科學(xué)測(cè)報(bào)和防治等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創(chuàng)新性地改變了小麥吸漿蟲的施藥策略并集成綜合防控技術(shù),并集成抗性品種、天敵保護(hù)利用等綜合防控技術(shù),進(jìn)行了大面積推廣應(yīng)用;創(chuàng)造性地建立了棉鈴蟲綜合防治技術(shù)體系,制定了“一代監(jiān)測(cè)、二代保頂、三代保蕾、四代保鈴”的棉鈴蟲防治策略和“加強(qiáng)測(cè)報(bào)、適時(shí)施藥、合理用藥、綜合防治”的抗性治理策略;原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我國(guó)農(nóng)作物病蟲草鼠害綜合防治技術(shù)研究需分三個(gè)階段發(fā)展的思想,即從以單種病蟲為對(duì)象轉(zhuǎn)變?yōu)橐砸环N作物的多病蟲為對(duì)象,再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以生態(tài)區(qū)多作物多病蟲復(fù)合群體為對(duì)象,使得制定的防控對(duì)策更加符合客觀需要;前瞻性地開展了棉鈴蟲遷飛機(jī)制、寄主植物-棉鈴蟲-天敵的互作關(guān)系研究,填補(bǔ)了中國(guó)對(duì)昆蟲觸角感受氣味物質(zhì)研究在分子水平上的空白,開啟了棉花害蟲基礎(chǔ)研究新領(lǐng)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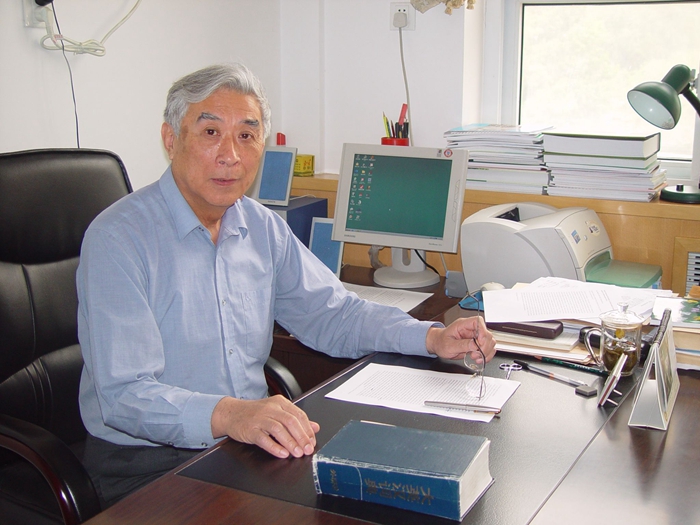
2002年,郭予元在中國(guó)農(nóng)科院植保所辦公室。中國(guó)農(nóng)科院植保所供圖
“老一輩的科學(xué)家們,都會(huì)長(zhǎng)期在鄉(xiāng)村駐點(diǎn),”吳孔明說,“他們?cè)谧魑锷L(zhǎng)季節(jié)長(zhǎng)期駐扎在鄉(xiāng)村和田間,冬季則回到實(shí)驗(yàn)室養(yǎng)蟲、做實(shí)驗(yàn),科研課題都是來自生產(chǎn)實(shí)際。我們今天紀(jì)念郭先生,就是要繼承他和其他老一輩科學(xué)家的精神,從實(shí)踐中出發(fā),去發(fā)現(xiàn)問題,結(jié)合自身的科學(xué)知識(shí)和素養(yǎng),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生治學(xué),以科學(xué)解決生產(chǎn)問題
吳孔明是郭予元先生的學(xué)生和同事,他博士后畢業(yè)之后就加入了郭予元先生的團(tuán)隊(duì)工作,對(duì)郭先生的生活態(tài)度、治學(xué)態(tài)度感觸深刻,“對(duì)學(xué)生的生活,他常常關(guān)懷備至,在科研上也總是給予最大的支持,他是一位開明而且包容的科學(xué)家,不會(huì)否定學(xué)生們的想法,哪怕他自己并不認(rèn)可,也不會(huì)反對(duì),而是讓學(xué)生們盡可能去探索,去學(xué)習(xí),在一次次的實(shí)踐中成長(zhǎng)。唯有一點(diǎn),就是不允許學(xué)生偷懶。”
中國(guó)工程院院士陳劍平在紀(jì)念會(huì)上說,他在年輕的時(shí)候就結(jié)識(shí)了郭予元院士,當(dāng)時(shí)郭予元已是名滿天下的大學(xué)者,“面對(duì)這樣的一位大先生,我剛開始很拘謹(jǐn),但郭先生非常和藹,經(jīng)常和我探討學(xué)術(shù)上的問題。他對(duì)學(xué)術(shù)問題非常嚴(yán)謹(jǐn),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象也有自己獨(dú)到的看法,且是非分明,是一個(gè)光明無限的人,今天的我們尤其需要這樣的精神,讓我們都努力活得純粹一點(diǎn)兒。”
郭予元院士的學(xué)生、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植物保護(hù)研究所梁革梅研究員談到她參加工作面試時(shí)與郭予元的談話,“當(dāng)時(shí)他問了我一個(gè)很尖銳的問題,是否能做到每年有半年以上時(shí)間到農(nóng)村調(diào)查、蹲點(diǎn)試驗(yàn)?后來到植保所工作后,我才知道這個(gè)問題并不尖銳,而是郭先生一生的工作方式。”
郭予元的治學(xué)與生活態(tài)度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家人,郭予元的三兒子郭大慶介紹,“父親的動(dòng)手能力非常強(qiáng),經(jīng)常幫助同事、鄰居修理鬧鐘、手表。對(duì)待工作,他非常刻苦和嚴(yán)謹(jǐn),總是積極樂觀,唯有一次我見到過他的沮喪,那一次,他養(yǎng)來做實(shí)驗(yàn)的蟲子全死了。但之后,他就很快振作精神,重新把蟲子養(yǎng)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