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事眼中,劉毓文和常玉曉是一對互補型的“創(chuàng)業(yè)CP”。中國農(nóng)科院深圳農(nóng)業(yè)基因組所的這兩位研究員,一位負責算法,有著豐富的創(chuàng)業(yè)經(jīng)驗,擅長路演宣講;一位負責實驗,在國內(nèi)外有著應用研究和產(chǎn)業(yè)化經(jīng)歷,承擔著實驗技術(shù)支撐。“科研不能是紙上談兵,如果做出來毫無用處,那做它有什么意義呢?”“科學家開公司不但不是不務(wù)正業(yè),反而是積極響應號召,把自己所學所得應用到生活中,以科技推動產(chǎn)業(yè),以產(chǎn)業(yè)推動發(fā)展。”同樣的想法讓他們走到一起。2022年10月,他們聯(lián)手創(chuàng)辦中農(nóng)芯躍(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立“萬相育種加速器平臺”。憑借這一加速器,他們在多個創(chuàng)業(yè)大賽中得到評委青睞。目前,對他們公司的天使輪投資正在盡職調(diào)查中。

劉毓文(左)和常玉曉。受訪者供圖
創(chuàng)業(yè)路上的相遇
“我一直在產(chǎn)業(yè)化的路上。”2014年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后,劉毓文就走上了創(chuàng)業(yè)之路。讀書期間,劉毓文領(lǐng)養(yǎng)了一只狗,但一直不知道它的血統(tǒng)。因為自己是做基因組研究的,于是他就想能不能通過測序得知狗的血統(tǒng)。“但動物基因組測序鮮有人研究,測序成本也比較高,很多普通家庭其實是負擔不起的。那時候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動物基因組測序的價格降下來。”劉毓文說,當時的他認為國外的寵物基因組檢測市場已經(jīng)風生水起,最領(lǐng)先的寵物基因檢測公司已經(jīng)拿到上億美元的融資,而國內(nèi)尚無這一行業(yè)企業(yè),會不會也蘊藏著巨大的商機?于是,當同班同學們紛紛進入科研界時,劉毓文卻決定放棄國外的科研職位回國創(chuàng)業(yè)。同學們都笑稱他要回國“賣狗”了。這一決定讓他的博士后指導教師甚為震驚。“當時我的學術(shù)成績還不錯,高分論文也不少。他一直以為我要搞學術(shù)。沒想到我要搞產(chǎn)業(yè)。”為了繞過國外的技術(shù)壁壘,劉毓文在自己家里搞研究,通過開發(fā)寵物液相芯片降低了部分測序成本。但由于國內(nèi)寵物基因測序市場并不成熟,第一次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走得并不順利。于是劉毓文決定回到他得心應手的學術(shù)領(lǐng)域,等待新的契機。忍受了芝加哥12年的嚴寒氣候,劉毓文選擇了深圳這個溫暖的城市重新出發(fā)。“我特別喜歡深圳,從氣候到環(huán)境到風景都讓我覺得很親切。深圳市政府對種業(yè)支持力度也非常大。”劉毓文說,基因組所的科研氛圍更讓他感覺“和在美國工作沒有什么區(qū)別,一切都很務(wù)實、透明、制度化,非常舒服”。他也如愿遇到了創(chuàng)業(yè)的新契機——在基因組所與常玉曉相遇,開啟了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之旅。“我們是在一起吃飯的時候認識的。當時就發(fā)現(xiàn)我和常老師夫人都是湖北宜昌人,而且家相距不到一公里。非常有緣,精準定位。”劉毓文回憶說。第一次見面兩人就聊起了基因檢測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當時的常玉曉正“猶豫著已有的成果要不要做技術(shù)轉(zhuǎn)化,因為轉(zhuǎn)化還是比較耗精力的”。對創(chuàng)業(yè)很有熱情的劉毓文恰好在這時候出現(xiàn)了。“我們兩個的互補性非常好。我原來是做植物的,他是做動物的。我們又有比較類似的知識背景,都做過醫(yī)學方面的研究。”常玉曉說。“我一直想找能夠跟我互補起來的人合作,互補才是1+1>2的效果。常老師實驗這一部分做得很好,而我自己在基因檢測實驗這方面不怎么做。”劉毓文說,“我們一拍即合,他負責實驗部分,我負責分析部分。”兩位科學家合作的目標就是:突破傳統(tǒng)的基因芯片技術(shù),達到高準確度和低成本的動植物個體基因型鑒定。他們發(fā)現(xiàn),兩個團隊的技術(shù)儲備經(jīng)過協(xié)作改良,通過“生物技術(shù)+信息技術(shù)”的整合,只需要花費現(xiàn)有方法一半左右的成本,就能在動物個體中檢測出1000萬~1200萬個遺傳標記,是現(xiàn)有芯片檢測數(shù)量的200倍,具有很強的便捷性和數(shù)據(jù)的穩(wěn)定性。就這樣,“創(chuàng)業(yè)CP”組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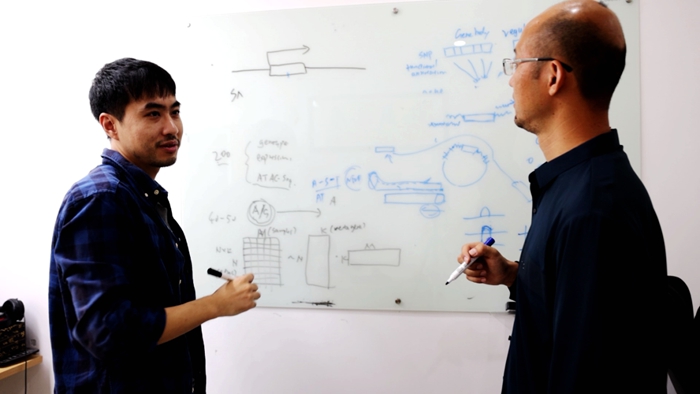
劉毓文(左)和常玉曉。受訪者供圖
“錯誤”的條帶創(chuàng)出低成本育種技術(shù)
近年來,基因芯片技術(shù)在動植物育種中得到廣泛應用。但是,“目前,基因芯片技術(shù)主要被國外的企業(yè)壟斷,不僅研究成本高昂,應用成本對于育種家來說也難以負擔”,常玉曉告訴《中國科學報》。基因芯片指的是通過微加工技術(shù),將數(shù)以萬計、乃至百萬計的特定序列的DNA片段(基因探針),有規(guī)律地排列固定于2平方厘米的硅片、玻片等支持物上,構(gòu)成一個二維DNA探針陣列,因為與計算機的電子芯片十分相似,所以被稱為基因芯片。以豬育種為例,采用國外育種公司篩查一頭豬的基因型就需要花費180元,育種的“整個群體測下來,可能就要花費上萬了,而且往往要測數(shù)百次甚至上千次才能得到準確結(jié)果”。常玉曉說,這是因為傳統(tǒng)的動物基因組檢測用的是醫(yī)學方法,難以大量應用,所以成本居高不下。“很多人沒有注意到農(nóng)業(yè)樣本的檢測和醫(yī)學樣本的檢測是不一樣的。”常玉曉說,后者是對個體單獨進行檢測,對準確度要求極高,也可以接受極高的成本;而農(nóng)業(yè)樣本是對群體進行檢測,相互之間可以參考,即使部分位點測錯了,也可以借助群體進行校正,因此,可以容忍一些錯誤,但絕對接受不了高價格。針對農(nóng)業(yè)樣品的基因型檢測,“創(chuàng)業(yè)CP”提出了‘以質(zhì)換價’的指導思想,在這個方向上開發(fā)農(nóng)業(yè)樣品專用的檢測方法。有趣的是,他們研發(fā)過程中一個關(guān)鍵技術(shù)的誕生居然來自一名研究生的誤操作。“當時她沒有理解我的實驗要求,有一個小步驟忽略了,她以為自己錯了,很忐忑地拿著‘錯誤’的條帶來給我看。”常玉曉說。結(jié)果,常玉曉一看覺得“有點意思”,雖然不是預期的結(jié)果,但是這個結(jié)果很好!于是他們對此展開了深入研究,最終創(chuàng)制了一個低成本的檢測方法。“我們自主研發(fā)的FBI-seq測序技術(shù),不僅簡化了文庫制備的流程,還極大地降低了文庫制備的成本,為高通量測序技術(shù)在育種中應用掃除了高成本障礙,解決了測序‘耗材成本高’‘技術(shù)難度大’兩大問題。”常玉曉說。

常玉曉 受訪者供圖
當平臺1.0版本做出來的時候,他們成功實現(xiàn)了植物基因檢測的低成本化。“但是我們還想解決動物基因組檢測的成本問題。顯然1.0版本對動物不適用。那時候我很著急。”劉毓文說。這時候,常玉曉提出來,在他此前的研究過程中,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一個更好的辦法,或許能夠讓動物基因測序序列的樣本在基因組分布更加均勻,從而更加適用于劉毓文開發(fā)的算法對數(shù)據(jù)的需求。于是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平臺2.0版本順利實現(xiàn)了對動植物基因組檢測的低成本化。他們把信息技術(shù)和生物技術(shù)結(jié)合起來,構(gòu)建Farm-Impute體系,又解決了“測序數(shù)據(jù)量大”這一大難題,通過降低個體檢測的數(shù)據(jù)量需求,進一步大幅降低了檢測成本,同時搭建了一個基于深度學習的多層級模型DeepAnnotation,從海量的基因數(shù)據(jù)中篩選、鑒定得到所需要的有效育種信息,近期又開發(fā)出了EmbryoGS體系,能通過少量胚胎細胞進行準確基因型分型,從而把基因組選擇的時間窗口提早到胚胎階段。。“隨著數(shù)據(jù)的不斷累積,模型會越來越完善,算法結(jié)果也會越來越精確。從最初的個人興趣出發(fā),到現(xiàn)在項目的發(fā)展,我逐漸意識到這項技術(shù)的意義不僅僅再局限于服務(wù)于個人、家庭,還與我們國家種業(yè)發(fā)展緊密相關(guān)聯(lián)。”常玉曉說。為了推廣這項技術(shù),劉毓文和常玉曉參加了幾次大型轉(zhuǎn)化項目路演活動和大賽,引起了企業(yè)的關(guān)注。目前他們的技術(shù)已經(jīng)開始在巴馬香豬等育種項目中得到應用。

劉毓文 受訪者供圖
保護+創(chuàng)新:雙輪驅(qū)動
“我個人認為,科技產(chǎn)業(yè)化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要根據(jù)產(chǎn)業(yè)的需求來制定科研的方向。”劉毓文說,如果天天坐在實驗室里搞科研,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很可能在產(chǎn)業(yè)里用不上,或者用處有限。“真正要做產(chǎn)業(yè)化,一定得去產(chǎn)業(yè)里邊看。”劉毓文說,他現(xiàn)在經(jīng)常出差“跑產(chǎn)業(yè)”,跑不同的育種公司,到牛場、雞場去看。“只有親眼看見那些動植物個體在田間和養(yǎng)殖場的表現(xiàn),跟育種企業(yè)家交流,你才能更清楚地明白到底哪些問題能夠解決,哪些問題是有價值的。一定要把方向選好。”對于科學家該不該開公司的話題,劉毓文認為,科技和產(chǎn)業(yè)就好像人的兩條腿,只有兩條腿一樣長,都有勁,才能走得穩(wěn)、跑得快。一個學科的發(fā)展也一樣,只有理論實踐雙驅(qū)動,才能獲得穩(wěn)定健康長久的發(fā)展。不過,常玉曉也直言,科學家開公司也面臨一些難以解決的困難:不具備專業(yè)的管理運營經(jīng)驗;精力有限,無法很好地兼顧創(chuàng)業(yè)和科研;產(chǎn)品轉(zhuǎn)化周期長,無法快速變現(xiàn)。為了做好產(chǎn)業(yè)化的運營,他們邀請了一位專業(yè)的運營管理人才加入,形成了一個三人核心團隊。此外,他們非常重視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工作,專門設(shè)置了一個部門負責相關(guān)工作。劉毓文說,目前他們已經(jīng)申請了多項專利保護,對核心技術(shù)進行了較好的保護。與此同時,他們還在不斷改進核心方法。“現(xiàn)在我們推到市場上的是我們的二代技術(shù),我們還儲備了第三代技術(shù)。”常玉曉說,他們一直在做新的開發(fā)工作,這樣即便被別人復制,而專利沒辦法很好保護的情況下,他們還留有后手,可以拿出新的方法來超越競爭對手。6月,在湖南長沙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教授賴錦盛提出,希望未來的基因型檢測成本能夠降低至10塊錢。“我們目前的技術(shù)對一個樣品進行基因型檢測的價格在150元左右,正在開發(fā)的第三代技術(shù)則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劉毓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