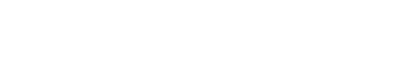國慶長假結(jié)束的第三天,距離北京以北1600多公里的呼倫貝爾國家野外科研臺站就迎來了今冬的第一場雪,白天的氣溫也降到零度左右。

呼倫貝爾國家野外科研臺站迎來冬雪。 侯路路攝
呼倫貝爾國家野外科研臺站的全稱是“呼倫貝爾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國家野外科學(xué)觀測研究站”,其主體建筑是兩座米黃色小樓,一座于2008年啟用,另一座主體建筑剛剛完工。這兩座小樓坐落在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qū)謝爾塔拉農(nóng)牧場的空曠草原上,是目前我國溫性草甸草原地區(qū)唯一的國家級野外觀測研究臺站,其依托單位是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農(nóng)業(yè)資源與農(nóng)業(yè)區(qū)劃研究所。
已經(jīng)在這里工作5個多月的“90后”碩士研究生侯路路,還在辦公樓內(nèi)整理此前從野外收集的樣品。5—9月是草原的生長季,也是呼倫貝爾草原國家野外科研臺站科研人員的野外工作季。從2017年起,侯路路每年從大城市來到這里,天天和小伙伴們早出晚歸,在臺站的放牧試驗樣地里忙活:調(diào)查樣方、測算牧草生產(chǎn)量;采集牛糞樣品、分析牛采食的情況……小半年下來,臉曬得像村姑一樣黑黢黢的。
“天天在太陽底下干這些活兒,苦不苦、累不累?”
“比起我的老師和師兄師姐們,我幸福多啦!”侯路路嘿嘿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起碼,起碼不像他們從前那樣到處‘打游擊’,有固定的地方吃飯、睡覺了。”
自1997年籌建、特別是2005年成為國家站以來,從首任站長唐華俊院士到現(xiàn)任站長辛?xí)云窖芯繂T,從“60后”楊桂霞、“70后”王旭、張宏斌、閆玉春、閆瑞瑞、徐麗君,到“80后”“90后”張保輝、陳寶瑞、徐大偉、李振旺、丁蕾、侯路路、沈貝貝等,一張藍(lán)圖繪到底、一茬接著一茬干,每年夏天都在草原上跋涉。

2008年夏呼倫貝爾野外國家科研臺站第一座辦公樓落成時部分人員合影。辛?xí)云教峁?/p>
“黑”是他們共同的面孔,“綠”是他們共同的目標(biāo):面對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家畜增加等多重因素導(dǎo)致的生態(tài)退化,把理論研究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相結(jié)合、在揭示草原生態(tài)演變規(guī)律的同時為農(nóng)牧民生產(chǎn)提供技術(shù)支撐,讓蒙古草原常綠長青。

呼倫貝爾草原國家野外科研臺站的“全家福”。 辛?xí)云教峁?/p>
開發(fā)數(shù)字牧場技術(shù),為牧民生產(chǎn)提供科學(xué)指導(dǎo)
“今天要回北京了,好興奮!女兒已經(jīng)考上大學(xué)了,回家要好好陪陪她,這些年虧欠孩子的太多了。
本來是晚上6點的航班,可是下午4點還在地里做實驗。這時突然下起了大雨,陳寶瑞和李剛還在特尼河的山上做實驗,我和辛?xí)云阶嚾ソ铀麄儯囃蝗幌莸侥喽牙锪恕N液蜁云揭黄鹜栖嚕屏私胄r也沒有推出來,只好放棄。我們在泥里走了一個小時才和開車來接我們的鄭永剛會合,他把我送到了機(jī)場。預(yù)定的航班已經(jīng)起飛了,我只好改簽晚8點的飛機(jī)。
我偷偷地到機(jī)場衛(wèi)生間把滿腳的泥洗掉,換上干的衣服。飛機(jī)晚點,到家時已經(jīng)是凌晨,女兒早就睡了……”
與辛?xí)云健安⒓缱鲬?zhàn)”近20年的同事、副站長楊桂霞在2008年7月20日寫的這則日記,記錄了呼倫貝爾國家野外科研臺站科研人員日常的工作、學(xué)習(xí)。

站在呼倫貝爾野外國家科研臺站的辦公樓前,
辛?xí)云胶蜅罟鹣歼@對并肩作戰(zhàn)近20年的姐妹格外開心。 趙永新攝
21歲在甘南草原,22歲在青藏高原,25歲至27歲在松嫩平原,28歲在南方草山草坡,29歲到呼倫貝爾……這就是中國農(nóng)科院農(nóng)業(yè)資源與農(nóng)業(yè)區(qū)劃所研究員、草地生態(tài)遙感團(tuán)隊首席科學(xué)家、呼倫貝爾站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之一辛?xí)云降目蒲熊壽E。自2005年呼倫貝爾站遴選為國家野外臺站,她就把這里當(dāng)做自己的第二個家。從常務(wù)副站長到站長,辛?xí)云胶蜅罟鹣几闭鹃L帶領(lǐng)年輕同事張保輝、王旭、張宏斌、閆玉春等,風(fēng)餐露宿、省吃儉用,一邊為臺站的基礎(chǔ)建設(shè)奔波忙碌,一邊把基礎(chǔ)科研與牧民生產(chǎn)相結(jié)合,開發(fā)、推廣數(shù)字牧場技術(shù)。
辛?xí)云浇忉屨f,所謂數(shù)字牧場,就是把信息領(lǐng)域的最新技術(shù)應(yīng)用到草原生態(tài)監(jiān)測和管理中,構(gòu)建草原上各種要素之間的定量關(guān)系,在更好揭示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機(jī)制的同時,對草畜生產(chǎn)進(jìn)行過程診斷和管理優(yōu)化,給畜牧業(yè)發(fā)展提供科學(xué)指導(dǎo),在提高生產(chǎn)效益的同時保持草地生態(tài)功能的最佳平衡狀態(tài)。
通過多年努力,辛?xí)云綀F(tuán)隊構(gòu)建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數(shù)字草業(yè)理論與技術(shù)研究體系,并制訂了草業(yè)信息技術(shù)領(lǐng)域第一個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開發(fā)出先進(jìn)的草地監(jiān)測與生態(tài)管理核心模型和系列軟硬件技術(shù)產(chǎn)品。
“辛老師他們搞的數(shù)字牧場正好解決了草場退化與畜牧超載的難題,很受牧民歡迎。” 陳巴爾虎旗畜牧和科技局黨組書記斯琴畢力格告訴記者,牧民通過辛?xí)云綀F(tuán)隊開發(fā)的專用手機(jī)APP軟件,就能預(yù)測當(dāng)年草地的產(chǎn)草量,然后據(jù)此決定養(yǎng)多少牛頭、什么時候出欄,既保持了草蓄平衡,又提高了放牧收益。“目前我們旗已經(jīng)有60多個牧戶用這個軟件指導(dǎo)生產(chǎn)了,覆蓋的草地有50萬畝左右。”
打草場改良、培育新品種,給牛羊提供優(yōu)質(zhì)飼草
“你看你看,這片改良后的打草場長得多好!羊草(內(nèi)蒙古草原最主要的優(yōu)質(zhì)牧草品種)又密又高,都沒過膝蓋了!”站在謝爾塔拉牧場公用打草場改良地里,陳寶瑞副研究員高興得要跳起來,“你看沒有改良的對照樣地,羊草長得稀稀拉拉的,對比特別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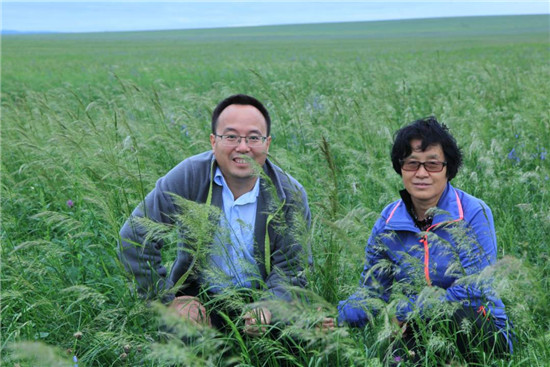
2019年8月,陳寶瑞(左)和楊桂霞在改良后的打草場留影。趙永新攝
2004年就到呼倫貝爾站讀研、工作的他告訴我:牧民使用的草原主要分兩種,一種是放牧草地,用于夏秋季放牧;一種是打草場,為牲畜提供冬春季草料。雖然打草場比放牧草地少很多,但地位極其重要。“由于年年打草、長期只有產(chǎn)出沒有投入,打草場也在退化,草長得越來越稀、越來越矮。在前期多年研究的基礎(chǔ)上,我們開發(fā)出一套草場改良的綜合技術(shù),從2016年起開始推廣應(yīng)用。”
“打草場改良的效果很不錯。”陳寶瑞說,2017年改良后的打草場每畝產(chǎn)草180公斤,是對照區(qū)的6倍;2018年,改良后的草場每畝產(chǎn)草量達(dá)到380公斤,對照區(qū)是80公斤。“改良后不僅草產(chǎn)量大幅增加,質(zhì)量也上去了。沒有改良的樣地羊草比例不到20%,改良后達(dá)到80%—90%。”
他介紹說,他們發(fā)明了成套技術(shù)體系,在草場上打孔、疏松土壤;同時根據(jù)草場的土壤情況,適當(dāng)施一些氮肥、磷肥、有機(jī)肥等,補充營養(yǎng)。“經(jīng)過這4年的摸索,我們的技術(shù)已經(jīng)成熟了,機(jī)械也不斷完善了,明年就可以大面積推廣了。”
其實,他們摸索的時間遠(yuǎn)不止4年。早在2009年,辛?xí)云健㈤Z瑞瑞和客座研究人員烏仁其其格就設(shè)計了退化草地改良實驗,并陸續(xù)發(fā)表了相關(guān)論文。基于這些摸索和研究,促成了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2013年公益性行業(yè)科技項目“半干旱牧區(qū)天然打草場改良與培育技術(shù)”立項,這是關(guān)于天然打草場的第一個國家級項目。
2013年開始,“70后”副研究員閆瑞瑞在呼倫貝爾站的草場改良試驗樣地上開展了系統(tǒng)的科學(xué)研究。當(dāng)年建立的樣地,現(xiàn)在依然管理的很好,仔細(xì)看去,試驗樣地上插著許多白色的小標(biāo)牌,每個小標(biāo)牌上有編號:W-1、W-2 、W-3,T-1、T-2……

2019年夏,閆瑞瑞和辛?xí)云皆诩?xì)雨中考察試驗樣地。 趙永新攝
“我是2008年到臺站做博士后研究的,跟著辛老師做牧戶調(diào)查、開發(fā)數(shù)字牧場,2013年之后專門負(fù)責(zé)天然打草場培育和改良技術(shù)研究與示范項目,為草地改良技術(shù)推廣示范提供科學(xué)基礎(chǔ)。”在涼颼颼的細(xì)雨中,閆瑞瑞邊走邊介紹:“這塊示范區(qū)分成若干個試驗小區(qū),有的采用物理改良手段,打孔疏松土壤;有的采用化學(xué)手段,添加化肥和有機(jī)肥;有的采用生物改良,用微生物肥料;有的三種手段都用,有的是什么手段都不用的對照區(qū)”。
“經(jīng)過這些年的研究,我們在理論研究上和技術(shù)開發(fā)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術(shù)體系。”閆瑞瑞說,“我們最終的目標(biāo),就是能夠為當(dāng)?shù)啬撩窠鉀Q冬季飼草缺乏這個難題。”
在改良天然打草場的同時,臺站的科研人員還在為人工草地培育牧草良種。
“這是紫花苜蓿,這是野大麥,這是山野豌豆……這些都是我們?yōu)榱伺嘤缕贩N引進(jìn)的材料。”在呼倫貝爾站后面的牧草栽培試驗樣地里,項目負(fù)責(zé)人徐麗君如數(shù)家珍。
她告訴我,由于草原退化,單靠放牧草地和打草場難以提供足夠的草料,必須栽培新品種、實行人工種草。“我們從2008年開始培育,現(xiàn)在已從全國收集了數(shù)百份材料、發(fā)現(xiàn)了許多‘好苗子’,特別是紫花苜蓿。”
她在一片開滿紫花的苜蓿地里蹲下身,摘下一個果莢、掰開,仔細(xì)數(shù)里面的籽粒:“這是我們剛通過區(qū)域評審、拿到新品種證書的中草13號,不僅抗寒,而且產(chǎn)量高、結(jié)籽多、適口性好,明年就可以推廣了。”

2019年8月,徐麗君(左)和她的助手烏仁其木格在查看紫花苜蓿的結(jié)籽情況。趙永新攝
“大家都說養(yǎng)孩子難,其實培育牧草新品種一點兒不比養(yǎng)孩子容易。”徐麗君笑著說,“即便是從引進(jìn)材料算起,育成一個新品種也需要十年左右,而且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享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苦,收獲著豐收的果實
為了草地上的“孩子”,徐麗君和同事們唯獨忘記了自己、冷落了自己的孩子。
到呼倫貝爾旅游的人都覺得草原美麗可愛,但在草原上搞科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夏天一般是科研人員休年假的黃金季,而對于在臺站工作的科研人員而言,卻是他們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工作季——整天在草地上做實驗、測數(shù)據(jù)、采集樣品……頭頂上是熱辣辣的太陽,周圍是嗡嗡飛舞、無孔不入的蚊蟲,他們穿著草綠色的野外工作服,一會兒就汗流浹背,臉上起包、身上長痱子是常事兒;到野外調(diào)查,由于車輛陳舊、道路崎嶇,顛得感覺五臟六腑都在沸騰;餓了就吃自己帶的干糧、咸菜,喝點涼水咽下;等做完實驗趕到下一站時,通常是半夜甚至第二天凌晨,只要能找到地方睡覺就感覺很幸福……由于長期風(fēng)餐露宿、吃飯沒點兒,好多人得了胃病;由于地處偏遠(yuǎn),楊桂霞的急性膽囊炎被多次延誤、疼得在床上爬不起來,最后不得不回北京做了膽切除……

為節(jié)省時間,侯路路(左側(cè)后)和小伙伴們在野外吃午飯。趙永新攝
建設(shè)臺站初期,由于經(jīng)費特別緊張,他們不得不節(jié)衣縮食,每人每周只供應(yīng)二兩肉,周圍的農(nóng)牧場職工聽說后傳為笑談;即便現(xiàn)在有了辦公樓,還要七八人擠一個房間;站里沒法洗澡,他們只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輪流坐車到農(nóng)牧場、市里公共澡堂……
說起這些常人難以忍受的苦,他們都淡淡一笑:這些真的沒什么,不苦不累還能搞野外科研?我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享受這個過程,體驗到了科研和發(fā)現(xiàn)的快樂。
但有一種苦,卻是刻骨銘心的,那就是與家人、特別是孩子的長期別離;對于徐麗君、閆瑞瑞等女同志來說,就更是難以忘懷。
“有了孩子以后,離別是對自己最大的考驗。我剛休完產(chǎn)假就要出野外,寶寶還沒斷奶,看到那么柔軟的小寶貝,真是舍不得走!離別了一段時間之后,我終于受不了了,最后說服家人、從臺站附近的農(nóng)戶租了一間房子,把孩子和老人一塊接了過來。忙了一天之后看到可愛的小寶寶,再苦再累都像打了興奮劑一樣,精神百倍。”說到這兒,徐麗君的眼圈紅了,不知是高興還是難過。
這些艱難困苦,都沒有擋住科研人員對科學(xué)的向往、對草原的熱愛。近幾年,除了徐大偉等年輕博士陸續(xù)加盟,呼倫貝爾站還吸引了多位“海歸”: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xué)的庾強博士、密歇根州立大學(xué)的邵長亮博士……他們的到來,極大拓展了臺站的研究領(lǐng)域,提高了呼倫貝爾站在全國和全球的學(xué)術(shù)影響力。庾強博士領(lǐng)銜建立了中國全球變化聯(lián)網(wǎng)實驗,用聯(lián)網(wǎng)實驗手段研究全球變化對中國及全球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和過程的影響,填補了國際聯(lián)網(wǎng)研究Nutrient Network和Drought Net在中國的研究空白,并在全球率先開展了養(yǎng)分和降水交互作用的聯(lián)網(wǎng)研究;邵長亮博士則建立了覆蓋呼倫貝爾及蒙古高原不同類型、不同利用方式的11套通量塔,將草原碳循環(huán)研究從臺站尺度拓展到區(qū)域尺度,并首次利用通量觀測開展了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熱浪研究。

徐大偉和他的兒子視頻通話。 趙永新攝
享受著研究的寂寞,也收獲了豐收的果實——2005年以來,呼倫貝爾國家野外臺站的科研人員累計發(fā)表論文483篇,獲得一批專利、標(biāo)準(zhǔn)和技術(shù)產(chǎn)品,并通過呼倫貝爾市政協(xié)、九三學(xué)社、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和中國科學(xué)院等,為當(dāng)?shù)睾蛧姨峁┳稍兘ㄗh10余份。其中“調(diào)整牧區(qū)建設(shè)思路,加大牧區(qū)建設(shè)力度”、“我國六大牧區(qū)的主要問題及對策-牧民財政補貼研究”等建議被采納,完善了我國草原生態(tài)建設(shè)和牧區(qū)工作的政策;
截至目前,臺站先后入選“國家牧草產(chǎn)業(yè)體系綜合試驗站”、國防科工委“高分遙感地面站”、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草地資源監(jiān)測評價與創(chuàng)新利用重點實驗室”、中國資源衛(wèi)星地面定標(biāo)場,以及美國宇航局陸地衛(wèi)星(Landsat)、歐洲航天局哨兵(Sentinel-2)衛(wèi)星、以色列(ISA)和法國地球觀測項目VEN?S等國際衛(wèi)星驗證站,并榮獲中央國家機(jī)關(guān)“青年文明號”稱號。
“其實我們更看重的并不是這些榮譽。”辛?xí)云秸f,“這個站是我國已故遙感生態(tài)學(xué)家、中國科學(xué)院院士李博先生倡議建設(shè)的。他生前曾說,呼倫貝爾草原是人類珍貴的自然遺產(chǎn),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天然生態(tài)實驗室。經(jīng)過這些年的工作,我們對李先生的話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感覺到這個站的價值和意義。”
“盡管還面臨經(jīng)費短缺等困難,但我們會在這兒一直堅持下去,而且一定會越做越好”。辛?xí)云秸f,“我們的近期目標(biāo),是希望在成果和產(chǎn)出上能夠達(dá)到國內(nèi)、國際一流臺站水平;遠(yuǎn)期目標(biāo),是希望呼倫貝爾站在草原上代代相傳,為蒙古草原萬古長青做出應(yīng)有的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