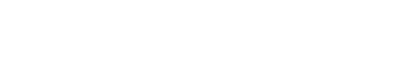“整棵棉花被吃得就剩下硬稈稈,葉子、鈴、花都被吃光了。”說到1992年,我國棉鈴蟲大暴發時的情形,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郭三堆仍然心有余悸,“那時,棉農大量使用農藥,開始的時候還可以,后來害蟲產生了抗性,根本毒不死。于是,小學生都放假去抓蟲子……”
盡管棉花害蟲的種類很多,但在1992年前,防治任務并不重。在此之前,棉花的一個生長季節,用農藥防治棉鈴蟲1—3次就足夠了,而當年則要防治20次以上。由于棉鈴蟲防治都在夏天氣溫最高的時候,棉農噴農藥時會出汗,農藥容易通過汗液進入人體,導致中毒事件的發生。據不完全統計,1992年—1994年間,農藥中毒人數超過24萬,每年給國家和棉農造成100多億元的經濟損失。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報道,河北省1992年的棉花平均畝產量是23斤,當時全國的平均水平是120—130斤/畝,絕大部分都損失掉了。我們作為搞棉花研究的科技人員,當時確實很心酸啊。”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長李付廣感慨地說。
郭三堆在一次調查中看到,一位種地的老漢,兒子兒媳婦噴農藥中毒死了,老漢還帶著孫子在種棉花。“當他們知道我們是從北京來的,而且我們告訴他一旦搞出抗蟲棉的話,將來就少噴農藥,甚至不噴農藥了,老漢馬上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從農村出來的郭三堆,很能體會農民的艱辛,也更堅定了搞抗蟲棉研究的決心。
基因構建篇 從單價到雙價融合
抗蟲棉的研究源自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的組織和實施。為了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和高技術競爭的挑戰,鄧小平同志發出了“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號召,并于1986年3月親自批準啟動了863計劃。
“863計劃包括生物、信息、材料、自動化等領域,當時農業還是生物領域的一個主題。所謂生物領域就是生物技術領域,那個時候生物技術正在興起,當時看出來,生物技術首先會在人類健康和農業上發揮重大作用。”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介紹說,“農業主題分為轉基因植物、轉基因動物和轉基因微生物三個專題。抗蟲棉研究被列為轉基因植物專題的一個課題。之所以把棉花列進去,主要是它的重大需求,另外當時專家委員會也注意到棉花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棉花在國外已經取得了很好的進展。上世紀80年代,國外公司已經把抗蟲的基因轉到了棉花中。”隨后的1991年,863計劃正式啟動了棉花抗蟲基因工程的育種研究。1999年,科技部和財政部聯合啟動了“國家轉基因植物研究與產業化專項”,轉基因抗蟲棉研發的支持力度有所提升。“十一五”期間,鑒于抗蟲棉取得的重大進展和成績,相關研究得到系統的重點支持,以“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為主,同時863計劃在上游的功能基因研究和轉基因前沿技術等方面給予了部署,加強了科技計劃和專項的銜接,大大推進了轉基因抗蟲棉的研發和應用。
姍姍來遲的單價抗蟲基因
在863計劃的支持下,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開始了抗蟲基因的研究。當時國外公司已經研制成功棉花的抗蟲基因,再加上隨之而來的棉鈴蟲大暴發,對是否引進國外技術存在兩派意見。
“其中一派認為,蟲害暴發這么厲害,國外已經搞成功了,直接把國外的技術引進來就可以用了,但也有一部分科學家,包括所里的范云六院士、賈士榮研究員都不能接受國外公司提出的高額專利費用以及對其市場開放的要求,都覺得應該自己搞,搞不成功最起碼還培養了一批隊伍。”郭三堆說,“剛好我在法國作訪問學者時研究的就是Bt(蘇云金芽孢桿菌)殺蟲基因的結構與功能。當時,863計劃項目抗蟲基因的研制,主要是密碼子優化和改造基因,參考專利,還是能夠完成的。”
當時我國的抗蟲棉研究處于起步階段,抗蟲基因的研制由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遺傳所三個單位承擔,但我們的軟硬件條件都很差,自行研制抗蟲棉并不被外界看好。到底能不能成功?什么時候能成功?這樣的疑問也迫使一些人產生過動搖,甚至離開了課題組。“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廢,拼了命也要把它搞成!”作為課題組的負責人,郭三堆的心中滿是堅定。
功夫不負有心人。1992年底,經過長達一年零八個月的刻苦攻關,郭三堆和課題組成員們根據Bt殺蟲晶體蛋白Cry1Ab和Cry1Ac殺蟲優勢結構域的氨基酸序列,采用植物偏愛密碼子,對基因進行修飾,在國內率先研制成功了GFM Cry1A 融合Bt殺蟲基因。1994年研究成功中國抗蟲棉,對棉鈴蟲等鱗翅目害蟲有很好的毒殺作用。
所謂轉基因單價抗蟲棉是指一種細菌來源的、可專門破壞棉鈴蟲消化道的Bt殺蟲蛋白基因經過改造,轉到了棉花中,使棉花細胞中存在這種殺蟲蛋白質,專門破壞棉鈴蟲等鱗翅目害蟲的消化系統,導致其死亡,而對人畜無害的抗蟲棉花。
“蟲吃了兩口,就不吃了,然后就中毒死掉了。傷口也很淺,甚至沒有傷口。而那個不轉基因的,因為沒有殺蟲蛋白,害蟲就猛吃,植株被吃得七零八落。”說起那時的情形,時任“轉基因作物性狀鑒定”項目仲裁的黃大昉仍然難掩激動,“當時我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把郭老師培育出來的第一批轉基因棉花植株,放在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的溫室大棚里作鑒定,把蟲子接上去后,就等著看結果。看到蟲子死掉了,我們都非常興奮。正是因為那次鑒定,大家信心倍增。后來轉基因抗蟲棉研究被列入863計劃重大關鍵技術項目,接著就是申請專利,安全性評價。”
自此,宣告了擁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單價抗蟲棉研育成功,中國也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個成功研育抗蟲棉的國家。
證明自己的雙價抗蟲基因
然而,事情遠非想像的那么順利。雖然我們已經取得國產單價抗蟲基因的專利,但卻遭到一些人的質疑。
“曾經有一段時間,有人懷疑中國的抗蟲棉有沒有自主知識產權。我們就跟他解釋:基因不一樣(當然最早的思路都來自Bt),另外載體不一樣,轉移方法也不一樣,品種還是我們自己的,這就構成了我們自己的產權,而且國際知識產權組織還授予過金獎。要是侵權了,還敢給你金獎嗎?而且國外公司都沒提出過我們侵權。咱們的知識產權還是相當過硬的。”黃大昉說。
“遭到質疑,當時是最難受的!”說起當時的情形,郭三堆有些無奈,“實際在任何時候,都有不同的看法。后來我們為什么要搞雙價基因,就是要證明,我們中國有能力研制成自己的單價抗蟲基因。唯一能讓人家相信的,就是開始雙價抗蟲棉的研究。”
此外,郭三堆表示,這項研究還基于另一方面的考慮:萬一抗蟲棉像農藥一樣,害蟲產業了抗性,就會失效,所以擴大殺蟲譜能夠減緩抗性的產生,于是從1994年完成單價抗蟲基因的研究之后,就啟動了雙價抗蟲基因的研究。
經過兩年的技術攻關,中國農科院生物所的科學家們將修飾后的蛋白酶抑制劑(CpTI)基因與單價Bt基因重新構建、整合,成功研制出雙價抗蟲基因(Bt+CpTI)。“雙管齊下”有效地增強了殺蟲效果,也大大延緩了棉鈴蟲產生抗性的時間。1999年,雙價抗蟲棉通過安全評價并獲準生產。
“搞完雙價以后,我們一檢測,兩個抗蟲基因有時高,有時低,后來我們認為,兩個基因是兩個各自獨立工作的表達盒,有時候這個高,有時候那個高,所以后來我們就將這兩個基因進行融合,融合成一個基因,工作起來就是一個融合蛋白。這樣一來,除了Bt殺蟲,引起害蟲消化道細胞裂變之外,CpTI還可以抑制害蟲消化食物,導致其營養不良,殺蟲更有效,后來我們就搞了融合基因。”郭三堆說。
2002年,融合抗蟲基因研制成功;次年,進入安全評價并生產試驗。課題組提供的數據表明,融合抗蟲棉對敏感性棉鈴蟲的校正死亡率可達94%,其對抗性棉鈴蟲的校正死亡率也是單價抗蟲棉的三倍還多。
轉化育種篇 從100到10000
基因構建出來了,科學家們又面臨著新的難題:如何將這些抗蟲基因轉入棉花中。
“作為產業鏈中游的中棉所和生物所的合作是從1996年開始的。最開始的時候,基因構建出來了,郭老師也申報了專利,有了自主知識產權,但是基因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如何讓它在棉花中變成棉花基因組的一部分,實實在在地遺傳下去,具有毒害棉鈴蟲的作用,轉基因操作這個環節就顯得非常重要,但是當時我們并沒有把這個環節克服,國內普遍都做得不理想。我們實驗室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始終難以突破。”李付廣說。
李付廣認為,三方面的因素導致當時國產抗蟲棉研究進展緩慢。首先,轉基因效率低、規模小。當時,我國轉基因植株生產規模小,基本上處于實驗室研究階段,當時的轉基因規模僅相當于國外公司水平的1/100左右,可提供的轉基因棉花育種材料很少,已成為培育重大品種的“瓶頸”。其次,我國棉花產業上中下游各自為戰,資源不能共享,低水平重復工作嚴重,阻礙戰斗力的形成。另外,產業體系不健全。我國絕大多數涉農企業幾乎都不具備完善的產品、服務和推廣網絡等系列配套環節,公司實力差且短視行為嚴重,多數公司“掙得起,賠不起”,根本沒有與國外公司競爭的實力。
轉基因技術實現高效規模化
針對我國棉花轉基因效率低、規模小,難以創造大量轉基因抗蟲棉花種質新材料提供給育種家研究利用這一重大“瓶頸”問題,2000年,科技部立項“棉花規模化轉基因及生物技術育種體系建立”研究項目,并由中棉所承擔實施。
“當時,轉基因操作并不成功,我們作為專門從事轉基因技術的工作人員,說實在的有一種無地自容的感覺。為了早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實驗室幾乎沒有節假日,可以說,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之外,都能看到我們實驗室有人在工作。大家憋著一股勁,就想著把它攻克掉。”李付廣回憶。
通過技術攻關,中棉所建立了棉花高效規模化轉基因技術體系平臺,可以同時采用農桿菌介導法、花粉管通道法和基因槍轟擊法快速獲得轉基因抗蟲棉新材料。據了解,花粉管通道法是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的“土生土長”的轉基因方法,這個方法雖然在理論上行得通,但因機理不清,實踐和理論差距很大。中棉所與江蘇農科院合作,通過大量田間實踐,使轉化效率大大提高。基因槍轟擊法是國外針對禾本科植物轉基因設計的,在棉花方面還沒有成功應用的實例。中棉所通過自主研發和不斷創新,在完全無菌的環境中,可以對棉花莖尖進行有效基因轉化。通過技術改進,農桿菌介導法轉化在關鍵技術上取得突破,使基因轉化周期由原來的12個月縮短到5—7個月,嫁接成活率達90%以上。
“當時的感覺很難一下子說清楚,既感到興奮,又有一種解脫的感覺,我們終于成功了!”李付廣高興地說,“在突破以前,年復一年的,總看到希望,卻始終差半步之遙。那是一種既看到曙光,又很難受的感覺。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一年大概只能獲得100多棵轉基因植株,到2005年,可以獲得將近6000棵/年。盡管規模擴大了,但效率并不高,后來,經過進一步探索,在幾項專利技術的支撐下,轉化效率得到進一步提高,目前可實現每年獲得10000棵以上轉基因的能力。”
通過該平臺,科研人員將抗蟲基因轉入到20多個主栽棉花品種中,轉基因材料遺傳背景大大拓寬;對轉基因棉花種質材料進行了快速篩選,將621份有育種價值的轉基因棉花新材料提供給育種家研究利用;通過轉基因材料的發放和與育種單位的廣泛合作,育成轉基因抗蟲棉棉花新品種30多個,促進了國產抗蟲棉研發水平的整體提升,競爭力大大提高。
抗蟲與高產的完美結合
“當我們搞成功單價、雙價及融合抗蟲基因后,我們就在想:我們的基因工程主要是解決什么問題?實際上,無論是抗蟲、抗病、抗旱還是抗鹽堿,其最大目的還是提高產量。因為我們國家‘人多地少’屬于剛性問題,只有把單產提高才能提高總產。后來我們就想與雜種優勢相結合。”郭三堆說。
據郭三堆介紹,現在的雜交棉都是手工去除雄蕊,由于棉花不像水稻小麥開花很集中,需要一朵花一朵花去去雄,先掰掉,然后授粉,不僅效率低,而且遇上下雨還會影響雜交工作,從而導致純度和產量降低。現在市場上賣的雜交種,有的純度還不到80%。
“在我們想利用雜種優勢提高產量的時候,發現河北省邯鄲市農科院已經從國外引進了一套三系(即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的材料。所以從1998年開始,我們就和邯鄲市農科院合作,利用他們提供的基礎材料,我們先后將單價、雙價抗蟲基因導入到三系棉花中,后來就搞出了抗蟲三系雜交棉。隨后便培育出我國第一個轉雙價抗蟲基因三系雜交棉‘銀棉2號’以及高產、多抗的抗蟲三系雜交棉‘銀棉8號’等新品種。”郭三堆自豪地說,“抗蟲三系雜交棉的研制成功,并能夠大規模應用,中國在國際上是第一個,這也宣告了原哈克尼西棉三系胞質不育的育性不穩、產量優勢缺乏及不抗蟲的難題被中國攻破了。”
“看到這個分子標記了嗎?這些分子標記就像三系抗蟲棉特有的‘身份證’,有了這個依據,別人再也不敢亂講我們的棉種是他們的了。”郭三堆說。
這是我國轉抗蟲基因三系雜交棉首次采用分子標記技術與常規育種技術相結合的生物育種技術。科研人員可借助差異序列獲得特殊的SCAR標記,用于辨別種子的真偽和歸屬。為保護育種者的自主知識產權提供了有力的科學依據。
數據顯示,抗蟲三系雜交棉不僅保持了抗蟲棉的特點,而且能提高品種的產量和品質,降低成本,可比常規抗蟲棉增產26%,制種成本降低一半以上。目前,抗蟲三系雜交棉已獲得專利保護。若每年種植5000萬畝,可增產皮棉80萬至100萬噸,約等于目前1000萬畝常規抗蟲棉田的總產量,相當于再造了大半個長江流域棉區,直接增收可超96億元/年。
新型抗蟲棉品種不斷涌現
“把抗蟲基因成功轉化到棉花中去,這只是個起點。搞育種常規的方法就是育種家從很多的材料中挑選,哪個材料更有發展前途,哪個材料適合哪個地區培育品種,只有材料多了,育種家才有選擇的余地。通過多年的努力,到2005年,我們實現了棉花規模化轉基因。現在,通過農桿菌介導法轉基因,基本可以做到一次就能成功。我們申報了5項以上國家發明專利,已經授權3項,這些成果使我們的轉基因效率提高了很多。達到了一次轉化就能出一批轉基因苗的效果。”李付廣說。
有了充足的材料,就可以進入到育種環節。“最開始育出來的種子,棉鈴雖然多,但很小,像葡萄一樣。農民不愿意種,最后通過育種的改進,把棉鈴變大了,抗病性也提高了。”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所長喻樹迅說。
說到育種,身為育種專家的喻樹迅深有體會。“在育種過程中,每個育種家都有自己的實踐經驗和靈感。盡管在大概方法上是相同的,但每個育種家在材料選擇上,有很大的不同。”
育種家的愛好、經驗決定他的選材,這里面有很多技巧。“育種家就像藝術家一樣,選擇的標準不一樣,有的時候就是憑借一種感覺,一種經驗。當然也有固定的標準,比如葉子多大,鈴多大,結鈴多不多等等。但是,棉鈴多了,結的小了也不行;棉鈴大了,結鈴數少也不行。同樣的東西,他能選出來,你不一定能選出來。”
“育種過程中,不成功是很多的。一年做幾百個組合都有,但成功的往往很少。有的育種家,一輩子也就育成一兩個品種,但他一年可能要做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組合。”
培育出品種后,看是否成功,還最少需要七八年時間的檢驗。“我們在海南島有試驗基地,利用該基地一年可以種兩次,所以可以把檢驗的時間縮短至三四年。新種子出來后,要把專家們組織在一起進行評定,和以前的品種進行對比,增產多少,是不是抗病,品質好不好。通過審定后再進行命名,這才算出來一個新品種。”
“十一五”期間,國家啟動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轉基因抗蟲棉的相關研發內容被納入到專項進行統籌部署安排。專項在轉基因抗蟲雜交棉、轉基因抗蟲早熟棉、轉基因抗蟲優質纖維、轉基因抗蟲特色棉等研究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其中培育高產、優質、早熟、多抗等各類抗蟲新材料594份,包括特早熟材料100份、2種以上復合抗性材料30份、優異纖維材料51份、創造不育系/恢復系材料50份等等。共審定轉基因抗蟲新品種49個。其中,中棉所41是國產抗蟲棉的典型代表,不但抗蟲性強,而且集高產、優質、抗病于一身,在品種區域試驗和生產中,比國外品種增產20%以上。
成果產業化篇 從5%到97%
“我們的抗蟲棉研究成功了,也跟有關部門匯報了,但他們不太相信。后來我們就把中國農科院植保所在河北廊坊的實驗基地作為對國內外示范的基地,每年開現場會進行宣傳。每年都種,種了以后讓大家來看,慢慢接受的人就越來越多。但即便是這種情況,當時生產部門還是有點猶豫。有些人不太贊成搞轉基因,擔心會造成環境污染;還有些人,對我們的成果不太自信。”黃大昉說。
而就在此時,某家跨國公司趁國內法規尚不健全之機,以合作為名,附加十分苛刻的條件,將他們的抗蟲棉產品先后打入我國植棉大省河北和安徽,并迅速占領了當地棉花市場。當時甚至有人揚言:“三年占領華北,五年占領中國。”
高技術和大資本結合的產業化模式
1997年,國外公司的轉基因抗蟲棉順利進入中國市場。1998年—1999年,迅速占領了國內抗蟲棉市場份額的95%,國產抗蟲棉僅占其中的5%。
直到1999年,國產抗蟲棉才進入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省市的植棉市場,開始大面積推廣應用。而真正在全國推開,是在2001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親臨中國農科院生物所,親切會見從事抗蟲棉研發的科技人員,并號召大力加快抗蟲棉的推廣應用之后。
“產學研”結合是高技術產業化的必由之路,轉基因作物育種產業也概莫能外。抗蟲棉具有高投入、高風險和高回報的特點,其成功與否最終必須經得起農業生產和市場的檢驗。在實驗室研究獲得初步成功后,如何讓抗蟲棉通過“高技術”與“大資本”的結合盡快走向生產應用,便成為研究人員和管理者面臨的首要任務。
黃大昉深有感觸地說:“當時發展抗蟲棉,科技部提出要實現高技術和大資本的結合。‘大資本’+‘高技術’,是一個整體的、大概的思路。我國棉農大量是小生產,種子公司也到處都是,具體怎么去做一直是我們在思考的問題。一開始沒想那么多,就想著把我們的成果給育種單位,讓他們賣就行了。后來覺得,這只是推廣應用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產業化。最后就考慮,怎么樣把我們的專利技術轉讓給公司,通過公司來經營。后來,我們堅持按照科技部領導的方向,去找大資本,找真正所謂的大資本。先找上市公司,后來找比較大的種子公司,都沒談成。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線,市場發育稍早,于是就找到深圳東方明珠集團。”
1998年,深圳創世紀轉基因技術有限公司誕生了,深圳東方明珠集團出資金、中國農科院生物所出技術。公司建立后,雙方的矛盾出現了。生物所希望公司快點推廣,能夠得到回報,而東方明珠集團則覺得生物所只給了他們品種的產權,而不是具體種子,也不一定賺到錢,所以也不愿意把應該投的資金到位。有一段時間,公司幾乎難以為繼。
創世紀真正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也只是5年前的事。2005年以后,公司引進了北京奧瑞金種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和他的團體,作為北京的民營企業,奧瑞金有一撥“海歸派”管理人才,他們有戰略眼光,有經濟頭腦,又有比較強的實力。他們進來后,對公司進行了清理整頓,使其真正成為一個高技術研發和產業化的實體。這樣一來,雙方按國際管理模式將資本和技術進行了完美的結合,推動抗蟲棉轉基因技術在全國大規模實施產業化。
“這個過程讓我感覺到,今后抗蟲三系雜交棉,如果沒有公司來進行產業化,肯定是不行的。”黃大昉坦言。
“我希望真正通過產業化把抗蟲三系雜交棉推廣起來,將來對我們整個棉花產業會是一個很大的促進。現在幾個國外大的公司都想找我們合作,想使用這項技術。我想,如果抗蟲三系雜交棉真正推廣開來的話,最受益的還是我們國家。知識產權、專利我們都有,而且能夠確保農民拿到的棉種100%是雜交種,有利于保護農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保護企業的利益。”郭三堆說。
全國一盤棋的研發推廣體系
其實,比做科研更難的還是如何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研發推廣體系。在中棉所搞轉基因抗蟲棉研究之前也有科研單位進行過這一研究,但收效甚微,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各自為戰,沒有形成合力。“必須把相關科研單位整合起來,形成一個拳頭出擊!”中棉所的領導在進行科研的同時,把很多精力放在了建立上、中、下游各單位的協作上。
身處中游的中棉所能與上、下游協作成功,關鍵在于他們采取雙贏互利的發展模式,通過合同關系,在尊重知識產權、成果利益共享的情況下,與我國從事基礎研究的多家上游基因構建單位開展了全面合作,一旦產生效益,都按合同規定的比例進行利益分配,很好地解決了知識產權問題。
“所里明確規定,利用上游構建的基因進行轉化后,轉基因課題不能搞育種,轉化后成形的材料,要交給育種家培育新品種,而育種家也不能搞產業化,而是由下面的公司統一來搞,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產業鏈條。最后公司再往上反饋利益,使抗蟲棉育種—遺傳轉化—基因構建有機結合起來。這樣一來,權利利益都解決得很清楚,‘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把全國的力量整合在一起,拳頭握緊了,力量就大了。”喻樹迅說。
合作體系的中游以中棉所為主,他們建立了棉花規模化轉基因技術體系,大批量創造轉基因棉花種質新材料,并將所獲得新材料快速發放給育種研究單位;國內多個棉花育種單位迅速培育出適宜我國不同棉區種植的國產轉基因抗蟲棉新品種。
體系的下游則是科技型棉花龍頭企業,中棉所科技貿易公司、山東惠民中棉種業有限責任公司、安徽長江中棉種業有限責任公司等企業經營新培育的轉基因抗蟲棉新品種,并通過轉基因抗蟲棉新品種的展示與示范以及建立遍布各棉區的營銷網絡,使國產轉基因抗蟲棉良種迅速進入市場,種到棉農的地里。
1999年,國家發改委啟動了“國產轉基因抗蟲棉種子產業化”和2002年科技部立項的“國家轉基因棉花中試與產業化基地”項目,均由中標的中棉所牽頭,一支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聯合艦隊”終于成功地建立起來了。全國“一盤棋”的研發推廣體系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最開始的時候,推廣并不順利。“開始時,棉農都不相信:哪里有那種事?棉鈴蟲會死?我們就讓公司去開現場會,做個比較實驗。一個是抗蟲棉,一個是非抗蟲棉,都不打藥。不是抗蟲的被吃得沒了葉子,就剩下光稈了,而抗蟲的葉子好好的,鈴多,產量又高,二者一對比,棉農慢慢就接受了。”喻樹迅說。
那時,國外的抗蟲棉,一是對中國的適應性不強,二是抗病性較差,有時會造成減產。而國內的抗蟲棉,通過改造,鈴變大了,本身又抗病,適應性也好,還比國外增產20%多,棉農也就不再愿意種國外品種了。這時國產抗蟲棉才開始“收復失地”,慢慢奪回國內市場。
經過10多年的努力,截至目前,國產抗蟲棉所占的市場份額已超過97%。值得一提的是,擁有我國Bt-Cry1A基因產權的創世紀公司與印度一家企業合作,于2006年聯合開發了多個雜交抗蟲棉品種,并獲準在印度3個棉花產區商業化種植,成為我國轉基因技術走出國門,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標志。目前,國產抗蟲棉與巴基斯坦建立了合作開發關系,與澳大利亞、越南等國也有合作意向。
經驗總結篇 行之有效的頂層設計
今年是863計劃實施25周年。在這25年里,我國的抗蟲棉研究在國家863計劃的大力支持下,快速成長,從“跟隨”到“領跑”,成果不斷涌現。自1999年以來,國產抗蟲棉產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遞增,截至2010年底,我國已通過審定的抗蟲棉品種共有300多個。黃河流域棉區與長江流域棉區的抗蟲棉種植率接近100%,國產抗蟲棉累計推廣面積達到3.5億畝,創造社會經濟效益500多億元,同時還有效保護了農業生態環境,減少了農民噴藥中毒事故。回顧我國轉基因抗蟲棉的發展歷程,有很多經驗值得總結、提煉。
黃大昉表示,在轉基因抗蟲棉的研發過程中,科技部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機制。科技部在技術發展方向、科技政策、管理制度等重大問題上統一決策,著力做好“頂層設計”;項目的具體實施和日常管理,包括研究課題評審取舍、研究目標確定、技術路線選擇、研究進度把握、工作績效考核、研究分配等由科技部下屬機關中心組織協調,并放手交由各領域專家委員會分工負責,全權操作。專家委員會成員來自不同學科,要求他們不僅學術造詣高、工作經驗豐富,有較強戰略思維與指揮作戰能力,而且學風正派、做事公道、在同行中有較高聲望;還激勵他們將高技術事業作為自己的“第一職業”而全力以赴。專家委員會高度重視宏觀戰略研究,反復研究如何“有所為有所不為”,認真選拔、培養和大膽使用優秀人才,積極引導上游基因研究與下游生產應用緊密結合,力求優勢互補,技術集成。正是有這樣一套理念和機制,終于組建起一支敢為人先,敢于攻堅的高技術生力軍,打贏了抗蟲棉等一場場硬仗。
當時,科技主管部門與相關產業部門之間也能做到統籌協調,相互緊密配合。例如,農業部從我國國情出發,建立了符合國際規范的轉基因安全評估與管理體系,使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迅速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在國際上贏得了好評。為了加快抗蟲棉研發和產業化進程,有關部門及時簡化了安全評價的申報審批程序,縮短了品種審定的時間,為這一成果搶占國際生物技術制高點和迅速推廣應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那時,專家和領導緊密配合,我們也經常聽取科技部朱麗蘭部長的直接指導,專家委員的考核朱部長也親自過問。我們當時勁頭也足啊,賈士榮先生當時說了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可見當時的專家和領導之間的關系非常融洽,配合得非常到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推進起來是很快的,及時地發現問題,及時地進行頂層設計。”黃大昉坦陳,“863專家委員會里,每一個人要擔任一個方面的責任專家,如賈士榮先生就是當時抗蟲棉研究的責任專家。責任專家權力很大,可以提出來經費使用計劃,這個計劃是動態的,專家委員會大概每二三個月開一次會,逐項檢查哪個課題需要多投錢,哪個課題要下,哪個課題要停。經過集體討論,最后科技部決定下一步我們的經費該怎么投,這套機制非常有效。”
“真正意識到人力資源的重要也是從863計劃開始的。國內在生物技術領域從國外引進了那么多人才,當時都是在863計劃的感召下下決心回來的。現在他們都是各行各業、各個單位的骨干。”黃大昉說,“大家都覺得,如果沒有當年的‘863’,咱們國內也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
“抗蟲棉研究取得這樣的成就,與當年863計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從抗蟲棉基因研究到遺傳轉化,從應用開發又到產業化支持都很大。通過項目的支持,我國轉基因抗蟲棉研究才能夠迅速發展壯大,把國外抗蟲棉占據的市場奪回來。”喻樹迅也表示。(彭東)